实现民族复兴征程中,文化自信深入人心,文化概念溯源待解?
作者:刘生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里,文化自信逐日深入人心,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独具特色,然而“文化”概念所指,依旧是一个值得予以关注的本源性问题,在此处进行些通俗的溯源以及比较,以此求教于方家。
“文化”,在汉语系统里,是古已有之的词汇,“文”跟“化”,一开始是分开的,分属于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
“文”,其本义是指那各色交错的纹理,也就是花纹,《易经》里说“物相杂,故曰文”,《考工记》讲“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这些所指的都是这个意思。在此前提条件上,“文”又衍生出若干层引伸含义:其一,是涵盖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类象征符号,进而具体演变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序》记载伏羲画出八卦,创造书契,“由此文籍得以产生”,《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文王已然去世,文化难道不就在我这里吗”,此皆为实际例子;其二,从伦理学说推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的意思,与“質”“實”处于对称对应关系,所以,《论语·雍也》称“质朴超过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超过质朴就会显得虚浮,文采与质朴二者协调得当,这之后才成为君子”;其三,在前面两层意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导出美、善、德行的含义,这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 ,郑玄注释“文如同美,如同善”,《尚书·大禹谟》所说的“文德教化遍布四海,恭敬地承受天帝的旨意” 。
“化”,其本义是改易,同时义为生成,还指造化,比如“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又如“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再如“化不可代,时不可违”,还有“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经过归纳,“化”所指的是事物形态发生改变,或者是性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还通过引申得出教行迁善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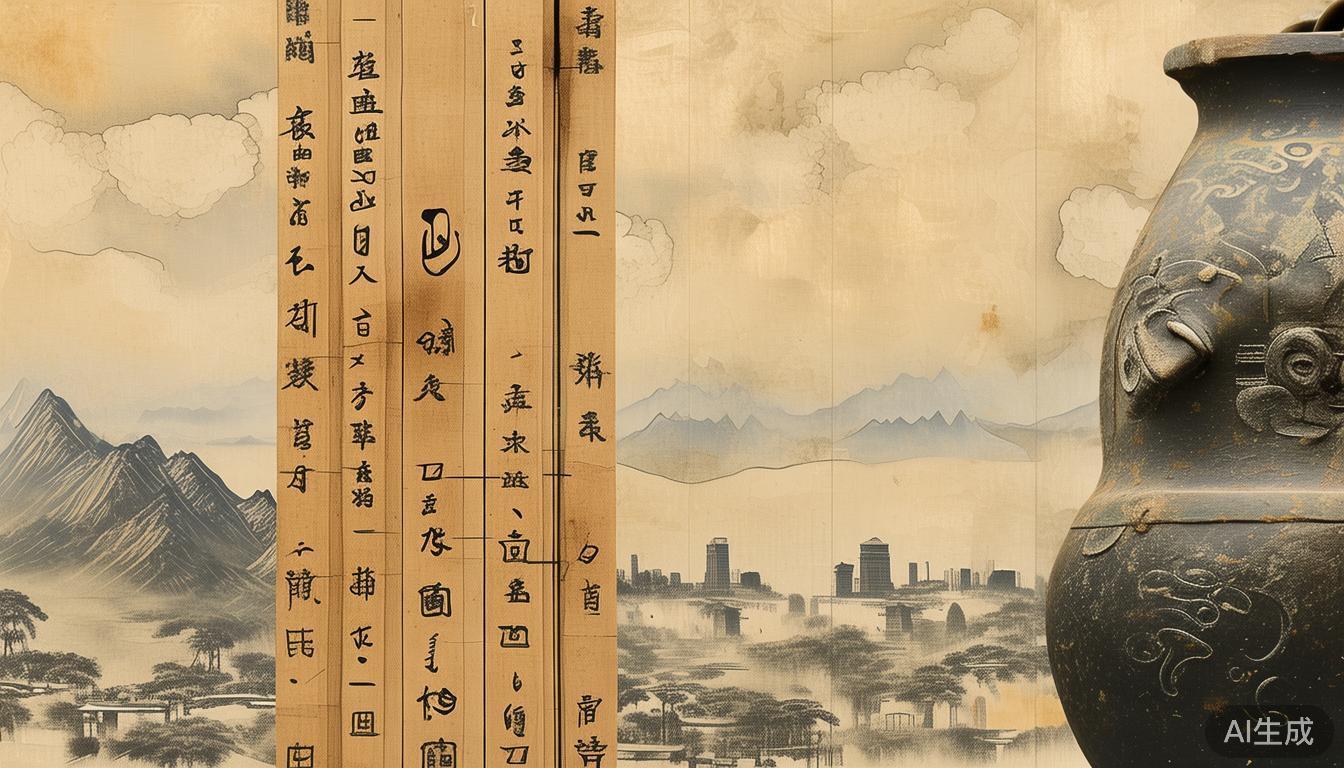
“文”跟“化”一块儿使用,比较早能在战国末年儒生所编辑的《易·贲卦·象传》里见到,其中提及“刚柔交错,这是天文。文明且能有所止,此乃人文。观察天文,用于洞察时变;观察人文,借此教化而成就天下”。西汉往后,“文”和“化”一开始并肩提出于是构成完整词语,像“文化若不改变,之后再施加惩处”“文化在内部聚集,武功向外部伸延”。这里面的“文化”,要不跟天然具备的自然进行对照,要不跟没有教化的“质朴”“野蛮”进行对照。所以,于汉语体系当中,“文化”的本来意义便是“以文教化”,其意味着对人的性情予以陶冶,对品德进行教养,原本属于精神范畴。经过时间的慢慢推移,“文化”渐渐变成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
长时间以来,人们于使用“文化”这个概念之际,其内涵存在很大差异也,其外延同样差异极大,所以文化一般有着广义、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文化是从人成为人的意义方面展开立论的,认为是文化的出现才把“动物的人”转变为“社会的人”,故而把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所有内容全部纳入文化的定义域。狭义的文化,通常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排除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里关于物质创造活动以及其结果的部分,实际上是把文化当作与政治、经济相区分的实体范畴,又被称作“小文化” 。20世纪80年代时,文化研究变成国内学术界的一股潮流了,文化概念的定义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了。总之,我们持有这样的观点,文化是跟自然现象不一样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含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以及非物质的东西。也就是说,自然界原本是不存在文化的,自从有了人类后,但凡经过人“耕耘”的一切通通都属于文化范畴。
在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得来的,原本含义是,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来满足食住等需求的进程之中,对土地进行耕耘、加工以及改良,后来,这个术语有了转义,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赛罗,在其“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里把文化的转义确切地表述了出来,智慧文化的内容变成主要指改造、完善人的内在世界,让人具备理想公民素质的过程。于是,政治生活被纳入文化概念,社会生活被纳入文化概念,培育公民具有参加这些活动所必需的品质和能力等内容被纳入文化概念,其内涵因此变得更为丰富。但在黑暗的中世纪,文化概念的含义遭神学观念压制,18世纪启蒙时代的理论家们将文化概念逐步从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自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变了,用法也变了。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有了新的意指,即“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美国著名文化学专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纵览各家、博采众长基础上,于《文化:一个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中,给文化下了个综合性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模式中,借助符号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且还构成人类群体特殊成就,这些成就涵盖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传统是通过历史衍生和选择得到的,其中价值观最为重要,这一定义被现代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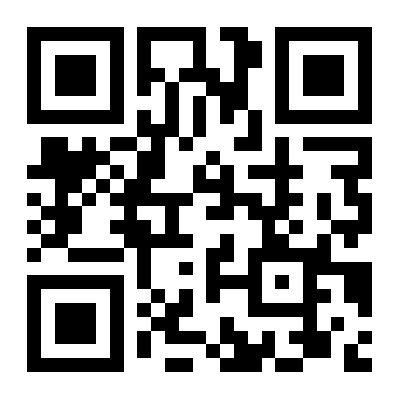
 请小编喝杯咖啡吧!
请小编喝杯咖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