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美术字成时代符号,今朝再遇书写场景,背后故事几何?
那似乎是很遥远的情景,那时黑板报、白墙壁、门框两旁等地,都是美术字大显身手的地方,机关、部队、学校、工厂、街道好像都有会写美术字的人,那时的美术字是时代政治最显眼的符号载体,也是汉字空间视觉史上最具冲击力的图景。我在中学读书时是美术骨干,负责出墙报、出大批判专栏,我会画题图、插图,可始终没写好美术字,一直为此遗憾。我在农村当知青时也是美术骨干,同样负责出墙报、出大批判专栏,会画题图、插图,却依旧没写好美术字,一直觉得可惜。没想到,社会告别美术字的视觉政治后,又遇到了要写美术字的场合。2007年春节前夕,我和同事、家人前往农村画“建设新农村”壁画,要按照过去宣传画的样式,在画面分别写上一些口号,比如“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生活保障的根本问题”,“农民可以成立自己的农会,与政府部门协商,共同建设和谐农村”,“尊重农民权利”,“民主选举,村务公开”等,这时我们一行人发现都写不好宋体的美术大字,只能勉强写上不太规整的黑体字 。时代确实不一样了,能拿起一把尺子、一粒粉笔头就在墙壁上写出漂亮美术字的人很少见了。这番回忆,是被一本关于美术字的书引发的,这本书由中央美术学院青年学者周博主编,书名为《字体摩登: 字体书与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再发现(1919-1955) 》,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17年9月出版。当然,这部难得的、图文并茂的著作,真正要帮助我们追寻的记忆,并不属于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而是属于那个年代美术字的前史 。
《字体摩登:字体书,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再发现(1919至1955)》
中国有着极为久远的文字传统,也有着极为久远的书法传统,然而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处于两者之间的汉文字字体设计宛如一段被遗忘的故事,那些曾为其贡献才华与努力的设计师的故事,似乎已随风飘散,那些艺术家的故事,似乎已随风飘散,那些作家的故事,似乎已随风飘散,那些业余爱好者的故事,似乎也已随风飘散 。其实,在那些字体背后,凝聚了现代性的几乎所有因素,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主义与个体自由、民族主义与文化漂移、理想与现实等冲突性的时代光谱,现代印刷工艺、大众商业文化、都市摩登审美、现代艺文发展、国族与政治的冲突斗争,以及激进、审美、功利、政治、精英、大众等现代语汇,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字体设计史的重要概念。从纯粹审美的角度去看,中文的字体设计有着和西方文字设计截然不同的形式逻辑,有着和西方文字设计截然不同的形象思维,其所蕴含的审美智慧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其所蕴含的艺术精神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这无疑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文化史,然而在当下我们的现代美术史叙事里,难以看到字体设计的存在、意义与影响,在商业文化史叙事中也是如此,在政治社会史叙事中同样如此,最终它只能附着在最后一批字体设计师的回忆、访谈等文字中。
《字体摩登: 字体书与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再发现(1919-1955)》是国内学界第一部专著,它从“字体书”(也就是美术字体设计书)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史,对七十多本颇为罕见的美术字体书籍进行了重新整理、编辑和研究,用现代设计的眼光审视并再现了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辉煌与演变。从专门研究、设计和推广美术字体的专书入手,这个角度有助于研究美术字体设计的流变,有助于研究美术字体设计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能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而且这些字体书中的字例更具设计精英意味的代表性。当然,如果能够继续分门别类地从生活中美术字体的具体运用来编集字体设计,能够继续分门别类地从生活中美术字体的具体运用来研究字体设计,那就更能让读者回到美术字体所依存的生活语境之中,更能让读者回到美术字体所装饰的生活语境之中。
该书论述的内容限定在1919年到1955年,起始年份是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收藏的1919年的《现代美术字》,终止年份是1955年方际青的《应用美术字资料》,然而作者设定这一时段并非是因为所藏的字体书 。作者在“绪论”中指出,目前难以确切说出美术字在中国的最早起源,不过现代意义上的中文“美术字”在清末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些出版物中已能见到。1955年是重要转折点,这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三十万份《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同年全国书籍报刊陆续完成从直排到横排的转变,终结了中国数千年文字书写和版式的次序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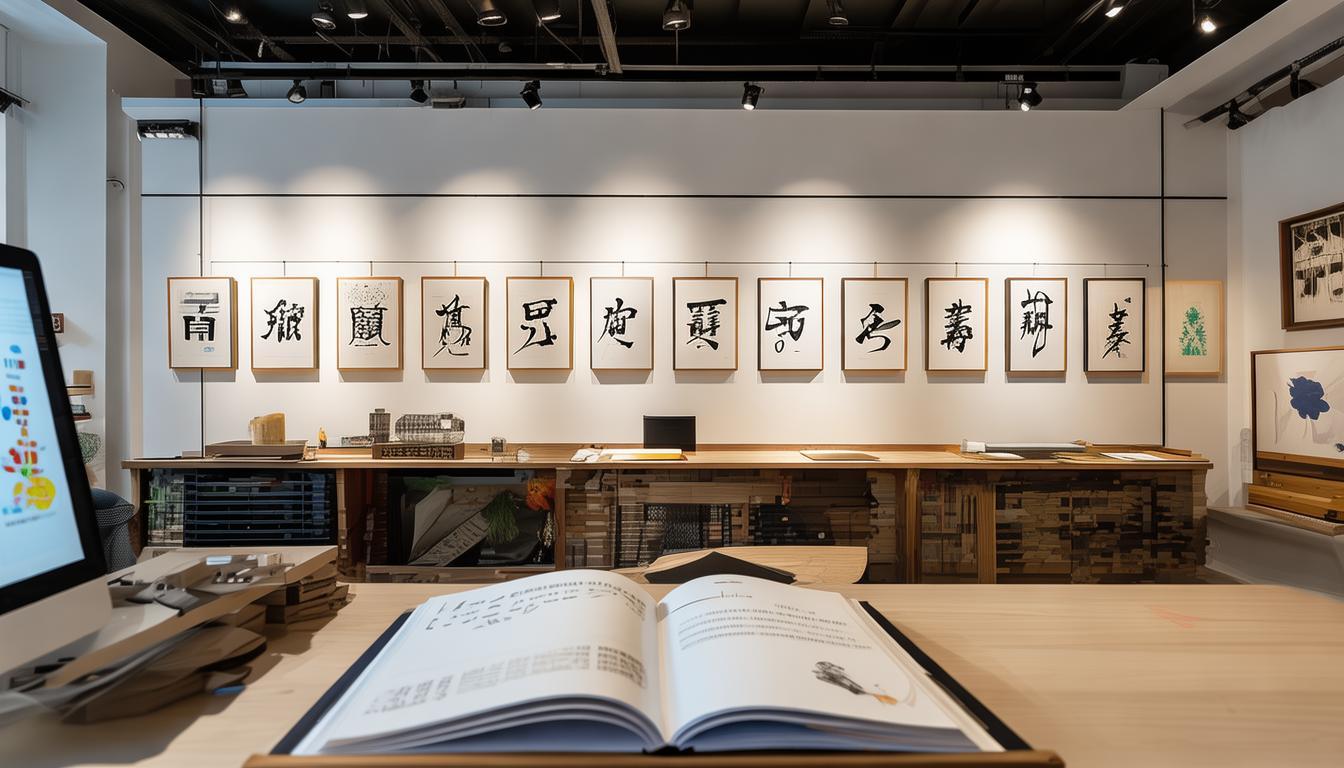
作者觉得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现代字体的设计历经了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的过程,时代的变化也在文字设计的内容与形式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能用“字体摩登”(Type Modern)这一概念来概括该时期文字设计的特点和成果,这是对本书书名的简洁阐释,即要探究中国现代字体设计的摩登风格以及早期面貌。在这个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美术字的复兴”,从设计史的角度而言,作者觉得,我们如今在研究中文字体设计时,一定要接上民国的美术字传统,要接上繁体字的设计经验,同时,最好对日本的图案文字也进行一番研究。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让“过去”回归“未来” (313页)
从政治和文化发生冲突的角度去看,这种“美术字的复兴”蕴含着相当复杂的内涵。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汉字现代“美术字”设计的繁荣与高峰时期,出现了钱君匋、陈之佛、张光宇、刘既漂等杰出艺术设计家,他们在商业文化、书籍报刊出版、社会文化活动等丰富的公共流通领域进行字体设计,充分显示出视觉文化先锋与中外文化合揉的时代气息,这是“过去”曾经的光荣。在四十年代以后,关于美术字的政治功能、宣传功能的要求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现,在“救亡”的时势中这种要求必然急剧增强,发展到五十年代以后它受到更为全面的和体制化的约束,美术字设计的“过去时”与“现在时”的分离是必然趋势。开始的时候,能看到有趣的现象,即使用民国的美术字、图案文字设计来书写新时期所需的标语口号,会有一种很不自然的扭捏之感。对此作者有两种分析的考虑路径 也许上海的字体设计师和出版商们是在用一种旧有的商业直觉 在“革命”的空气中寻找着一种别样的商机 但是许多著作的内容和形式都表明 他们对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宣传政策实在是所知寥寥 (179页) 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的确更大
在该书所收集的“字体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有趣的例子。方仲卿的《新名词美术字》第13页有“文工”这两个美术字,若不看下面的图案,即吹拉弹唱的人物图案,可能一时联想不到“文艺工作者”;第31页的“表扬”,在第195页也是以美术字形式呈现的“新名词”,在这里能发现与新政权紧密联系的“新名词”,也是必须通过字体设计来加强传播效果的。更有意思的是,字体设计者们确实从形象性与审美效果的角度,极力强化文字内容的政治性意义。比如禇堤所著《怎样写美术图案字》第40页呈现的是“秋风扫落叶”,每个字中间都镶嵌着一片或者两片树叶,并且笔画的粗细变化以及字形笔势的侧斜都能让人感受到瑟瑟秋风的感觉。陆亦祥所著的《抗美援朝美术字标语》第199页中,有“不听”“追究”“谣言”的组合,该组合将视觉焦点落在了“谣言”身上,此内容在第209页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为美术字体设计的字例,很多取自流行的政治口号。比如,傅天奇《新中国图案字谱》第21页是“不居奇,不投机,巩固物价稳定”(249页)。又如,姜宝泉《应用美术文字编》第52页有“控诉日寇旧罪行,反对美帝新阴谋”(252页)。再如,王东《新美术字》第15页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73页),此内容来自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讲话:“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美术字设计的时代变化并非只体现在表面的字体、字例方面,事实上,美术字在20世纪50年代初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即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图案字做法要接受无产阶级文艺方针的“改造”。田自秉所著的《图案字作法》,傅天奇所著的《新中国图案字谱》,这两本书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建国之初,前者最早强调要改造旧有的图案字,后者是被官方的《美术》杂志发文点名批判的对象”。(179页)从那以后,用作者的话讲就是“我们‘断’得已经看不清来时的路了” 。其实,那种千姿百态的字体设计,有浪漫的、商业的、守旧的,所谓“来时的路”的字体设计,确实无法适应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的需要,只能将统一、简单、快速、有力和战斗性作为字体设计的最高要求。这就是我们在70年代初所崇拜的“会写美术字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们完全是在一个时代的断层上认识和使用“革命”美术字体。
除了在手写美术字体上展现出强烈时代性,我们还记得在印刷字体中也要突出高度政治意识。例如,不知从何时起,书籍报刊中只要引用革命领袖原话,就必须用黑体字印刷。直到1978年4月,教育部下达一份通知,这份通知是“关于教材中引用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语录字体问题的”,该通知不再要求在文章中引用这些语录时,以黑体字特别标识出来。另外还想到,在手写的大字报、大标语里,那些要打倒的“走资派”“阶级敌人”的名字,通常是要颠倒着写的,然而在书籍报刊的印刷中,似乎没见过颠倒过来印的情况,也许这只是我见识少?
把美术字写得让人难以辨认,这确实是个问题,是对“来时路”的反思,在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宣传标语、图画上都存在,作者在书中用一些具体例子分析了此问题,田汉于1938年曾批评某些美术字标语,称“乡下人连正字都认不清楚,美术字当然更看不懂了。”艺术家常常有这毛病,为了满足自己,把客观的政治任务忘记了。这话说得很对,然而这个问题早在1934年蒋介石于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时就已被提出,国民党中央向各地方政府部门传达了蒋介石亲自颁布的指令,指令要求所有部门发行的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一概不准使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以及外国文,并且对于文中涉及中国问题的部分,更不许使用西历年号,以此来重视民族意识。1939年12月,行政院发布一道训令,要求各学校机关此后“一切标语皆应刊写正楷文字,以资一律而利宣传”。毛泽东于1942年撰写《反对党内八股》,谈到党内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时,首先批评的例子是钟灵在延安城墙上写的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 。其中的“工”字,中间的竖转了两道弯,“人”字,右边一笔加了三撇。毛泽东认为,这种字的写法是在故弄玄虚,目的是不想让老百姓看懂 。其实,有很多字例远比“工”、“人”的例子更难看懂,比如1933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的布钞三串的背面有“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字样,见李明君所著《中国美术字史图说》233页,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这些字样看上去很有设计感,所有字样都非常图案化,然而一般人难以辨认。又比如,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学联第一次代表会议”的会议大标题,其笔画粗细有极端变化,笔画方圆有极端变化,结体也有极端变化且呈现图案化,(同上,235页),但也只是让人勉强能看懂罢了。应该说,千姿百态的创造性与自由表现的创造性,和某些必须肩负实用功能的通俗易懂性,并非无法相容的极端,关键还是要有不同使用语境的针对性,应该建设时代文化氛围,应该维护时代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既容纳千姿百态,又不忽视实用功能。
美术字设计怎样应对当下的电脑时代,以及未来会更全面渗透到日常生活里的人工智能时代,这无疑是平面设计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现代艺术与文化史的研究者而言,不能遗忘的是从摩登到革命的字体设计史中所发生的故事,因为这更是“有字为证”的历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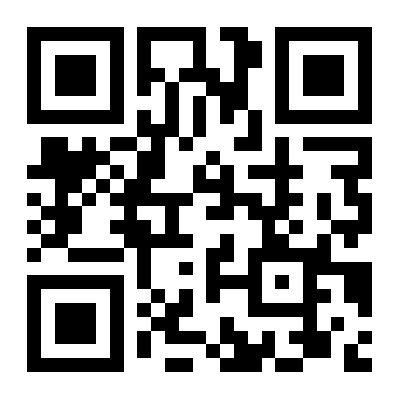
 请小编喝杯咖啡吧!
请小编喝杯咖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