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旧藏拍卖引涟漪,拾掇旧书,品味往昔情调
艾芜《南行记续篇》插图一(吴冠中绘)
艾芜《南行记续篇》插图二(蒋正鸿绘)
杨朔《生命泉》题图二(袁运甫绘)
杨朔《生命泉》题图一(袁运甫绘)
《包法利夫人》插图
《新儿女英雄传》书影
《巨手》插图(袁运甫绘)
周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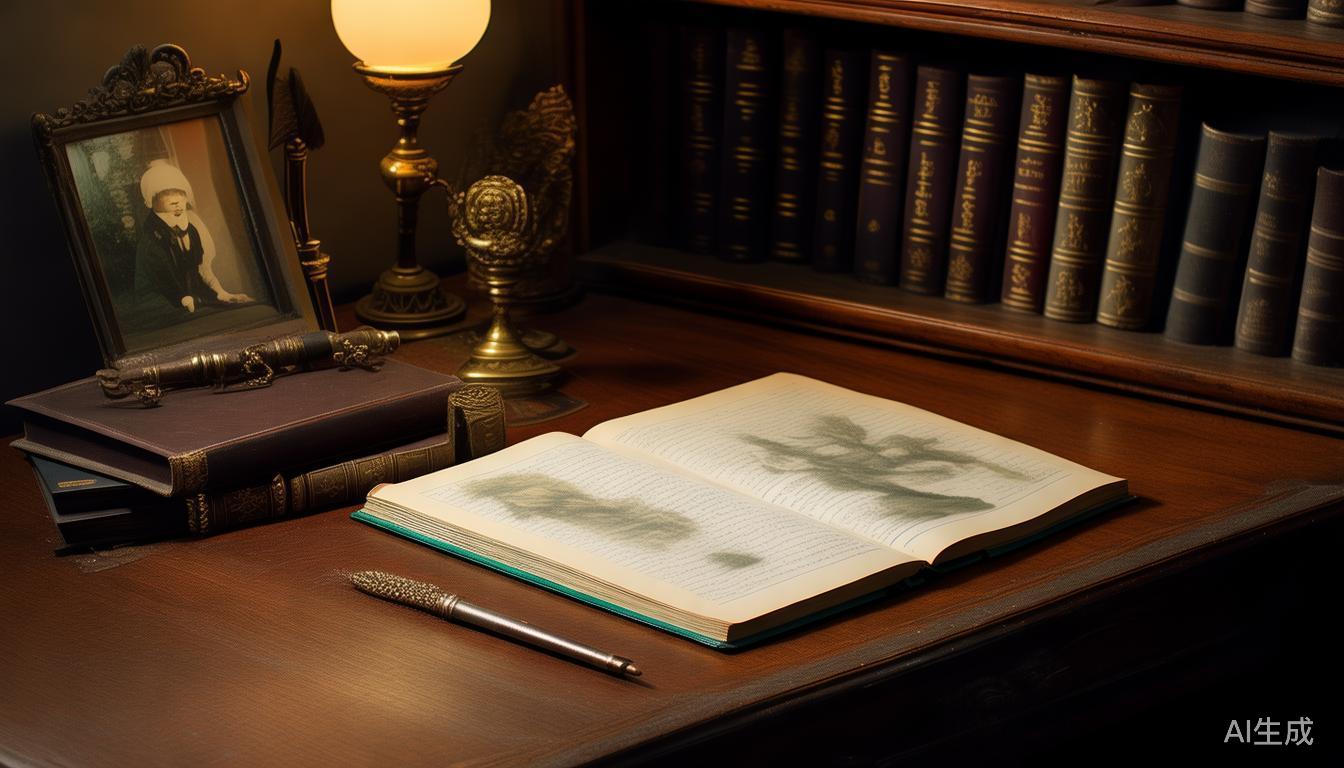
近日,京中藏书大家姜德明先生的旧藏进行拍卖,这激起了不少的涟漪,追忆之中,与姜先生一次次聊天,他兴致勃勃讲述的都是书前书后的故事,对印装的精美赞不绝口,对插图和设计同样赞不绝口,这让我多少品味出了拾掇旧书刊的三昧,那并非数钞票,而是得有一点情调,才不辜负那些饱经岁月风尘的旧书刊,为了这么一点小趣味小情调,我愿不时翻起那些有着各种图画的旧书,由此向着往昔时光进发。
拾掇旧书总得有一点情调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翻译契诃夫的小说,还说,这回翻译所抱的主意,并非是为了文章,倒不如讲是因为插画,德译本的出版,似乎也是出于插画的缘故。这位插画家玛修丁(V.N.Massiutin),是最早把木刻给中国读者鉴赏的人,《未名丛刊》里《十二个》的插图,就是他的作品,距今大概已经有十多年了。“老头子”甘愿降低自己的身份,宣称自己的翻译只不过是“插图的说明”:“契诃夫的这一类小说,我已经介绍过三篇。”这种轻松小品,中国恐怕早有译本,可我是为别目的:原本插画大概是作品装饰,我翻译只当插画说明。”(《〈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406页)这般买椟还珠,鲁迅堪称超级玩家。我东施效颦,流连书肆常为插画买书。一些小册子,别说收藏家,一般人都瞧不上,我照收不误,不避过时应时,回家捧着发黄书页看得津津有味。
当年旧事,豪华的插画阵容
关于鲁迅喜爱图画这件旧事,讲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不必再去说了。我想要表达的是,那一代的文人在审美方面都是达标的,而且有着许多共通一致的爱好嗜好。比如说巴金,他主持经营文化生活出版社,还创办了平明出版社,致力于翻译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著作,尽管对外宣称是为平民大众出版书籍刊物,可是呢,所出版的书籍并非粗陋简陋,许多名著都精心挑选了插图配图,虽说处于当时那个 era,印刷的条件极大地制约限制了图像的印制呈现效果,然而精美漂亮的插图与优美雅致的文字相互融合浑然天成,依旧还是能够让人喜爱倾心到爱不释手的地步。对于他印行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9月初版)我是较为喜爱的,这其中配有法国Pierre Laprade所作的插图,看上去那像是钢笔线描画,其细部呈现出密不透风的状态,而疏处广阔到能让马肆意奔跑,它和世界名著那种格调以及文字极为契合,常常会将我引诱至小说人物深邃的内心深处;平明出版社为巴金妻子萧珊所出版的译作《别尔金小说集》,配有俄国的水彩插图,使人刚翻开就能够感受到普希金笔下那令人震撼的大风雪。
那个时代的画家纷纷放下身段,还放下润笔,愿意为书刊配图。这种风气至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都颇为兴盛,往后大家就都默不作声了。黄永玉的版画集中,有一大部分是他为文学作品所配的插图。1959年,中国出版界有一次壮观的豪举,即为郭沫若的《百花齐放》出版了木刻插图本,该版本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59年4月出版 。把刘岘、李桦、王琦、力群、马克配上黄永玉这些木刻家,在今天给他们冠以“大师”的名号,人们都不会有意见吧,这些木刻家为该集中 101 首诗都配了插图了,这插图就像一个盛大的画展,难怪作者在后记中这么写道,“我要做一次特别提到,感谢《人民日报》编辑部同志们有过的鼓舞,我还要感谢他们动员了好些同志去作插图” 。并非只有达到郭沫若那个级别的作者才能够享有这样的待遇,当时书刊的插图差不多是标配,而且薄薄的小册子数量众多,出版社也并没有因为其小、薄就轻视它们,相反在每个环节都投入了诸多心思。《新儿女英雄传》,在当时算得上是流行小说,我手头的这本海燕书店在1950年10月出版的第八版,其封面以及扉页之上“袁静、孔厥合著”并列的是“彦涵插图”,由此能够看出插图属于该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牧的一本《巨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8月版),封面和插图都是出自画家袁运甫。袁先生之作,线条明快,其中带有现代感,非常富有装饰性,适宜用作插画。
《南行记续篇》是艾芜所著,由作家出版社于1964年9月出版,文前明显有插图目次,其阵容堪称豪华,其中包括:野牛寨的插图是吴冠中所作,芒景寨的为蒋正鸿所作,姐哈寨的是徐启雄所作,边疆女教师插图乃姚有多所作,边寨人家的历史插图是由袁运甫所作,雾的插图是柳成荫所作,群山中插图也是柳成荫所作。像吴冠中这样后来在市场上画价极为高昂的画家,其画作被用于做插图,在当年也是常见之事。《郭小川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12月出版第2版,其插图便是吴冠中所作。可惜的是,那些书涵盖诸多世界名著,在后来重新印刷、改变排版成为新版之后,其中的插图都踪迹全无,往昔编辑与画家耗费的心血付诸东流。近些年来,风气发生转变,插图本、珍藏本纷纷出现,插画好像有再次兴起的态势。我感到不满足之处在于,这些都是豪华装帧、“珍藏版”,不像是给普通人阅读的,甚至只是打算让人“珍藏”,而非想要人们日常去阅读。实际上,美应该在日常生活里展现出生命力,也唯有如此才最具生命力。我依旧怀念那些平常的小册子,还有平装本,从中同样能够体会到豪华的,以及精心的装帧阵容。在冬天的时候 ,午后时分,泡一杯热茶,有意无意地翻开来,那样才会惬意。
赏心悦目的题图和尾花
不是只有插图,环衬、题图、尾花这些美术元素加进来,增强了一本书的美感与艺术性,这样的小书拿在手里,文图相互映衬增色,翻开给人一种收获之感。图书的装帧设计,并非仅在封面、版式,它还展现在诸多细节里,属于整体设计。像扉页、环衬,现在好多书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净”,只有如墨猪般呆滞的书名等信息。别忘了,这也是一本书的门面呀,恰似推开门走进来第一眼看到的 。辛笛的诗集《印象·花束》,其版本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版,拿在手上摊开扉页,左右是相连着的状态,衬底颜色为深绿色,书名处在右上位置,出版社位于左下位置,页面上铺满了线条,这些线条显得凌乱却是有所表达那般,看上去既像抽象的“印象”,又仿佛是具象的花束。袁运甫为秦牧设计封面、所作插图的《巨手》,其扉页上部存在一个田字格子,书名以及作者名占据了对角的两个格子,另外两个格子是设计者精心绘制而成的线描画,该封面艺术气息十分浓厚。
非常值得怀念的题图和尾花,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它们虽都是比较简单的装饰性图案但它的存在让单调呆板的文字页面有了活气,犹如在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上开了一扇窗。这些零零碎碎的小图常常不过是闲花野草,然而却是装帧者手绘,它的手工感又让机械的印刷中留下人的踪迹使一本书变得亲切可感。这些年遇到这种有题图尾花的小书我甚至都不关心内容直接拿下。这本书是袁运甫为杨朔作插画的《生命泉》,由作家出版社于1964年6月出版,这本不过100多页的小书,却给人带来精美绝伦的感觉,书装的装饰风格极强,且不说这个,单看每篇文章的题图,作者一点都不肯马虎,紧紧扣住文意,还画出自己的特色,这使得全书在文字之外,再多出一套可供欣赏的系统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套小开本散文集,无论是作者还是内容,都自然而然地吸引人们的目光,我对它们的题图,以及尾花这些小装饰,怀着深厚的喜爱之情,书卷气之中,灵动气息并不缺乏,于小细节里,全书的品位得到提升。书中开本尺寸小巧,正是因为这些,当人们翻开书页时,仿佛能够使人置身于花草繁茂昌盛的原野,自然而然地拥有一番与众不同的别样感受。1979年5月第二版的叶圣陶所著《小记十篇》,书前《再版说明》里提及:“初版时所刊载的照片,在再版的时候全部予以撤销,改为每一篇都增添题头图一幅。”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决定,手绘题图所具备的艺术感远远超过照片。孙犁所著《秀露集》,该版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1年3月出版,此书诸多文末存有小小的尾花,其采用的是小花小草,并不复杂,带有自然气息,这跟孙犁平淡、自然的文风极为契合,能给人带来赏心悦目之感。
当年书刊存在明显短板:纸张质量欠佳,印制技术比不上当下,特殊工艺更是极为罕见。然而,如今各项基础条件优于过去,我们的图书却缺失关键的艺术感、手工感与书卷气,全成电脑制作、流水线上的标准件,甚是乏味,亦缺情调。这便是我像九斤老太那般愈发爱去翻阅那些时间愈发久远的出版物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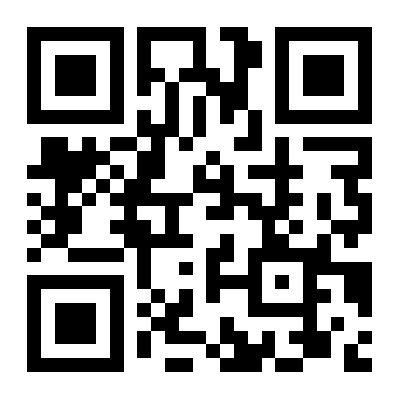
 请小编喝杯咖啡吧!
请小编喝杯咖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