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书籍封面引发的精神触动与思考?
在我高中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存在主义思想为那些渴望精神滋养、沉迷自我放逐且陷入绝望境地的年轻人提供了心灵的慰藉。《恶心》与《局外人》这两部著作,它们以平装书的形态承载着浓重的焦虑情绪,它们的封面设计,如同宗教图像触动信徒心灵一般,对我产生了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非如宗教图像那般使我心灵得到升华,反而让我感到忧郁。书籍的封面本应与读者在精神层面产生共鸣,然而,现实中却鲜有封面能够真正触动我的内心。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初期,正值美国“高品质平装书发行”阶段,众多严肃小说以及非虚构纪实作品的封面上,出现了引人注目、激发读者想象的指示牌式设计。这些设计,与那些普遍可预测、刻板且缺乏读者个人解读空间的精装书相比,更是在书籍的个性化特征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恶心》与《局外人》的封面上,巧妙地融入了象征意味和令人不安的神秘气息。《恶心》的封面设计出自伊凡·切尔马耶夫之手,由两张营养不良者的高对比度头像组合而成,黑白相间的照片不仅生动地诠释了书名,而且即便过去四十多年,该书依然能够持续出版和销售。《局外人》的封面上,利奥·李奥尼绘制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抽象面部速写,它巧妙地激发了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孤独情绪,然而遗憾的是,这本书现已售罄。这两部作品对存在主义进行了阐释,却并未对书中的内容进行详细的指引。精装书籍常配备内容夸张的插图,而热门读物则可能采用过于俗套的装帧,然而,大多数高品质的平装本却展现了非凡的洞察力和精致的设计,尽管如此,这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读者进行深入思考的空间。
《恶心》封面
切尔马耶夫、李奥尼、保罗·兰德、阿尔文·勒斯蒂格、米尔顿·格拉塞、西摩·切瓦斯特以及鲁道夫·德·哈拉克等人的创作,与平装书的风格有着极高的相似度。这些设计师和插画师在各自出版商和艺术总监的激励下,将极简主义、抽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理念引入出版领域,从而催生了一种更为规范的出版形式。他们由此对根深蒂固的市场法则发起了挑战,并且开始注重对字体大小以及色彩搭配等细微环节的挑选。
二战结束之后,大规模销售的平装书行业出台了相关法规,吸引广大读者群体要求封面设计降低信息量,转而采用类似日场电影海报的浪漫与伤感现实主义风格,即便是威廉·莎士比亚的情感丰富的戏剧作品也不例外。与此同时,高品质的平装书需要在大学生群体和虔诚的普通读者之间探索新的销售途径。安可出版社在1947年推出的精装平装书,采用了更优质的纸张和更为牢固的装订技术,对经典和绝版书籍进行了再版。因此,这些高品质平装书的封面设计,必须借助抽象插画以及宽泛的现代主义排版风格,打造出一种文雅的视觉表达。这样的设计不仅提升了书籍的整体品质,而且并未使其变得罕见。
亚瑟·艾伦·科恩,当时年仅23岁,却是一位勇敢无畏的年轻人。1951年,他与几位好友携手创立了正午出版社。紧接着,在1954年,他又与伙伴们共同创立了子午线出版社。他提到,对他而言,坚守出版行业的传统规范,抵制追求“好设计”的诱惑,实则轻而易举。他所指的,是在既有的精装书出版领域内,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让平庸的设计方案占据书籍封面的关键位置,追求的是吸引眼球而非启迪思想。科恩委派阿尔文·勒斯蒂格以现代化的手法负责设计正午出版社及子午线出版社的众多封面,此举显著提升了高质量平装书封面的整体设计水准。1955年,勒斯蒂格不幸离世,随后伊莱恩·卢斯蒂格接替了他的职位。
科恩曾明确指出:“众所周知,平装书的问世仿佛注定要摆脱传统出版业的束缚。”这场被称为“平装书革命”的变革,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展开,尽管并未彻底颠覆旧有的出版规范,却显著地改写了出版业的惯例,对美国民众的阅读习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现今,大学生们有能力购买到轻便的经典著作,科恩将这种现象称作“平装书教育”。昔日一度绝迹的诸多重要书籍,如今有了更多重见天日的机遇。部分出版商甚至为上乘的平装书量身定制了新颖的标题,而非最初便将其印制为精装本,这使得创新设计和排版工艺显得尤为关键。
企鹅出版社,作为英国平装书界的领军者,采纳了扬·奇肖尔德在1946年所创的排版方式。这种格式摒弃了繁复的设计,转而以“斯巴达式的庄重”为特色,尽管它声名显赫,但灵活性却相对不足。这种方式塑造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故企鹅出版社在内容差异上不拘泥,统一采用统一的版式设计和有限的色彩来处理所有书籍的封面。科恩指出,这种“简约而又略显乏味”的设计有其独特之处:“任何视力正常且具备阅读能力的人都能识别,只要封面上那两个蓝色区块被一块包含书名和作者信息的白色区域分隔开来,那便可以断定,该书出自企鹅出版社之手。”在那时,市场上的每家出版社都正不遗余力地推销他们的书籍。在这样的嘈杂和混乱的氛围中,企鹅出版社所采用的谨慎的推销策略,传递出一种坚韧、自信和难以逾越的形象。然而,科恩却刻意让自己的著作不显露出企鹅出版社那种“普遍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及那种更加明显的“反复出现的时尚”风格。科恩与企鹅出版社所倡导的“禁欲主义的自律”持不同意见,同时,他也对一种趋势表示了抵制,即那些仿佛直接从《纽约客》杂志广告中摘取的、整洁光鲜的照片和木刻画在书封上占据了显著位置,而印刷格式则显得不那么重要,陈词滥调似乎也将持续存在。科恩对高品质平装书的评价,其深度源于现代平面设计所赋予的独特风貌。
阿尔文·勒斯蒂格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将超现实主义的蒙太奇摄影技巧与保罗·克利、琼·米罗风格的抽象字体,巧妙地融入了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 Books)的精装本封面设计之中。随后,他在为子午线出版社与正午出版社的平装书封面设计时,转而采用了19世纪折中主义风格的木材与金属排版。与莱斯特·比尔早期所创排印相仿,勒斯蒂格的书籍封面采用了粗衬线字体以及铁路哥特体的结合,偶尔还会模仿古时雕刻家的手稿。此外,他常将对比强烈的色块与条纹置于深紫、橙黄及栗色等不常见单色背景之上。
简约被视为一种品质,书籍必须能在与其它书籍,甚至唱片封面和贺卡等物品的激烈视觉较量中脱颖而出。在一系列尚未公之于众的手稿中,勒斯蒂格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更倾向于不去追求超越其他华丽设计的浮夸,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独特的视觉对象”,而这个对象恰好就是一本图书。将书籍并排放置,封面朝外展示在书架上,同时确保书籍之间有恰当的间隔,以增强氛围感。他强调,标题特意采用小写形式,以避免与精装书封面上大写的字母相冲突,以此维持其高雅气质。然而,勒斯蒂格的整体布局更为关键,那些设计虽不具典型性,却蕴含象征意义,并流露出传统秩序感的微妙韵味。它们致力于追求独特的新鲜感和难以归类的高雅特质,而非仅仅模仿那些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或传统风格。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于平面设计师来说,上乘的平装书籍等同于现今的CD封面,它们不仅是独特的,更是设计灵感的重要来源。《发行人周刊》刊载了1957年美国平面设计协会(AIGA)在设计师角色研讨会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该声明明确指出:我们现今的CD包装设计秉持着“书籍应即时阅读,因此我们不应试图为遥远的未来进行设计”的原则。古典书局(Vintage Books)曾是当时最关键的高品质平装书出版机构,其封面设计工作则由艺术总监哈里·福特(Harry Ford)以及制片人西德尼·雅各布斯(Sidney Jacobs)共同负责管理。保罗·兰德被邀请为一家经典书局设计封面,这一设计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他巧妙地运用了抽象的拼贴艺术和富有表现力的幽默素描。这些独特的艺术手法并不随波逐流,而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基于游戏性和经济性考量所选择的。在封面设计上,他选择用小幅海报来阐释书籍内容,而非直接绘制插图。
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的《超越墨西哥湾》一书,其平装版封面设计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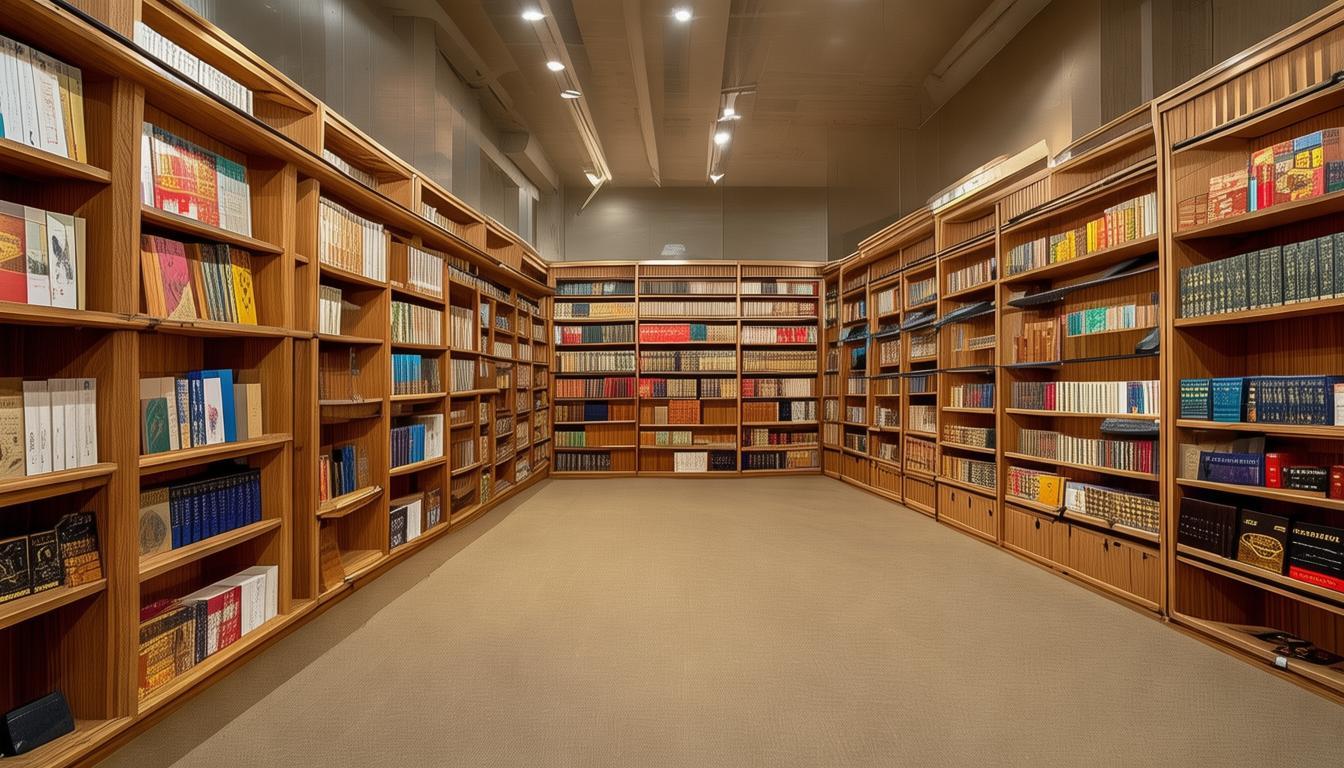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风格的古典书局封面设计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这一潮流的兴起,得益于保罗·兰德、利奥·李奥尼、伊凡·切尔马耶夫、本·沙恩、布拉德伯里·汤普森以及乔治·吉斯塔等众多设计师的共同努力。相较数年前,众多书店如今纷纷大力推广高品质的平装本,而在此之前,勒斯蒂格的封面作品在书架上几乎是独树一帜的平装书。由此可见,封面设计已无法如勒斯蒂格所预想的那般保持一致,折衷的设计风格却逐渐盛行开来。
伊凡·切尔马耶夫在求学期间担任勒斯蒂格的助手,他不仅协助勒斯蒂格设计封面,还独立创作了原创封面,对现代主义和折中主义的设计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恶心》之外,他还为新方向出版社的众多封面进行了设计,并在其中尝试了蒙太奇照片的运用,拓展了其应用的可能性。他运用了印刷中的双关技巧,为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艺术总监弗兰克·梅茨设计了多款封面,其中一款便是《戏剧性书写的艺术》。在这幅设计中,他巧妙地用感叹号取代了所有原本的“is”字。文字的双关运用能极大地将书名转化为文字游戏,原本难以形象化的概念得以通过这种方式转化为直观的图示。借助这种方法,切尔马耶夫将书籍的封面设计转化为了他进行创新发明的试验田。
埃里克·弗雷德里克·戈德曼所著《关键的十年及其之后:美国1945-1960》的平装版,其封面设计引人注目。
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叶,鲁道夫·德·哈拉姆进行了实验,他利用约350本平装书的封面拼凑出了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McGraw-Hill)的标志性设计。这一创意受到了瑞士设计理念的启发,他运用了一套严谨的基础网格系统来安排版面布局。在此基础上,他运用富有象征意义和预示性的比喻手法,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广泛纪实主题进行了阐释。随后,他深受达达主义、抽象表现主义以及错视觉艺术运动的启发,将这些风格与手法融入了自己的设计之中。网格系统使得德·哈拉克得以对概念艺术与摄影实验的范围进行有效控制。因此,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的封面作品成为了现代主义纯粹主义晚期的代表,此后的众多出版商旗下封面设计师纷纷效仿。
1964年,作为图钉工作室(Push Pin Studios)的联合创始人,米尔顿·格拉塞迎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他被委以重任,负责为广受欢迎的莎士比亚戏剧系列普及版设计一系列封面,这些封面将采用现代风格,并配有插图。艺术总监比尔·格里高利(Bill Gregory)期望“印象莎士比亚系列”(Signet Shakespeare series)的封面设计充满趣味,格拉塞回忆说,书籍封面的设计是有顺序的,这样的设计能够营造出一种氛围,使得这些封面在书店中能够被集中展示。然而,此处却呈现了一个更为神秘的突破性进展,格拉塞如此阐述,“当时,精装本的封面很少采用四色印刷技术,而平装本则可以运用这一技术”,因此,他精心设计了一幅莎士比亚角色的彩墨画像,画像外围环绕着白色的边框,上方装饰有彩色的条纹,内部则包含了标志性图案,从而使得书籍易于辨认。
莎士比亚经典作品系列《奥赛罗》封面
格拉塞表示,封面设计需具备直观性,他坚信它不应过于抽象,亦不宜过分强调排版。此外,它还需具备吸引力,无需模仿市面上多数畅销书那种平凡的外观。莎士比亚作品的畅销得益于其封面插画,而这些书籍的亲民价格也让“印象系列”在中学与大学课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受“印象系列”的引领,众多平装本畅销书出版商纷纷重印了众多严肃文学与纪实文学作品,并在这一新兴领域采纳了更为繁复的设计与插图。与格拉塞相似,图钉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西摩·切瓦斯特在为各类主题和不同作者的书籍设计封面时,运用了折中主义风格的图像。切瓦斯特回忆说,平装书带来了一种创新的可能,没有人向我传授具体的方法,他们仅划定了边界,并将自由发挥的权利交给了我。因此,每一款设计都与主题完美契合,比如,我会把关于南太平洋的书籍封面设计成具有原始风格的画作。在为阿尔贝·加缪的悲剧性存在主义戏剧《瘟疫》设计封面之际,切瓦斯特采用了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将封面呈现为一幅荒凉的木刻画。他表示:“我无法创造出过于精致、繁复的设计。”通过这种忧郁的艺术风格,他直接展现了加缪内心的焦虑情绪。为了撰写神秘主义者乔治·葛吉夫的传记,作者巧妙地将中东地区充满灵性的书法艺术与自身的折衷主义个人风格相结合。切瓦斯特通过其多变的艺术设计,向世人传递了一个信息:在这个艺术领域,一切皆有可能。
在20世纪40年代,那些广受欢迎的平装书籍初露锋芒之际,出版界竟然恬不知耻地断言它们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坚信它们注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纵然高品质的平装书并未立刻扭转大众对这类书籍普遍持有的“一次性消费”观念,但它们在平面设计上的质量却彰显了更为严谨乃至可能更为长久的内涵,这无疑对读者产生了极为正面的影响。精装书籍的声誉将持续不衰。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些高品质的平装书封面,它们不仅是创新现代主义的发源地,更是其象征,它们在设计的自由度和独创性上甚至超越了精装书的护封。最终,平装书封面赢得了设计师们的敬意,并且对现今所有书籍封面和护封的设计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经授权摘自《设计良质:解码平面设计》,标题为编者所拟。
《设计之精粹:揭秘二维设计艺术》,由美国作家史蒂芬·海勒所著,李义娜与宫小迪联合翻译,出版自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发行于2021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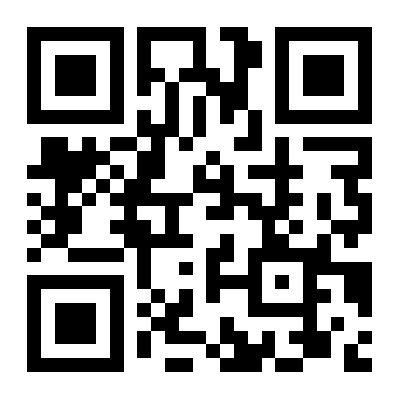
 请小编喝杯咖啡吧!
请小编喝杯咖啡吧!